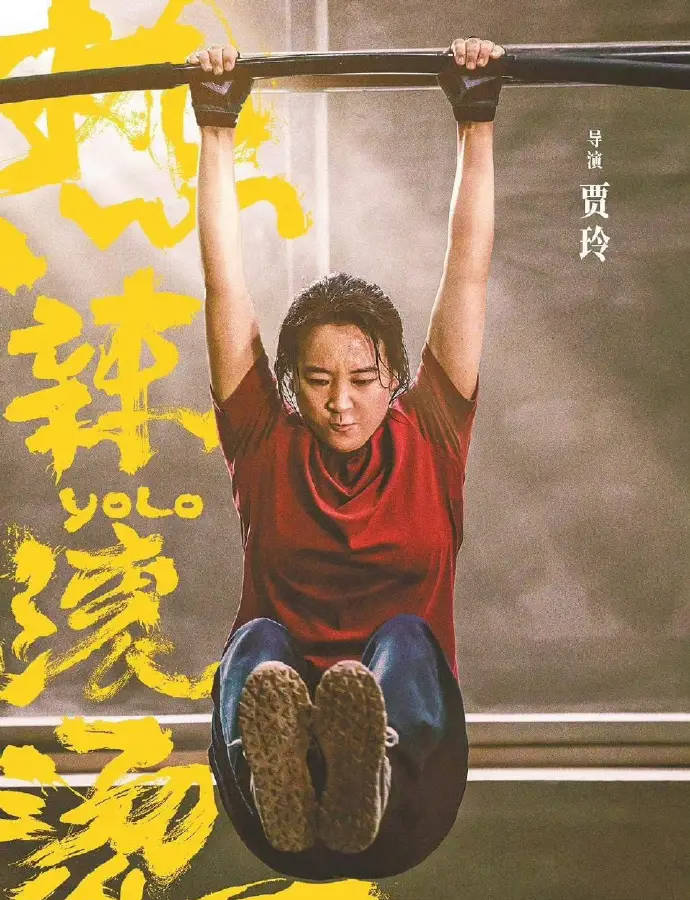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1年02月11日 08 版)
年俗是传承,在漫长的历史中孕育;年俗是文化,承载着先人的智慧与愿景;年俗是乡情,因神州大地的广阔而多姿多彩;年俗是祝福,祝人人康健、家家祥和。
今天,大地副刊为读者奉上“年俗”专版,以文学笔触展现缤纷年俗,共庆多彩佳节。
编 者
腊月红
赖赛飞
我们管这种红叫腊月红,浓缩为本,点睛为要,类似往雪白江米团子尖上、往纯真孩童的眉心中间点上一点朱砂红。
腊八节一到,所在的小城里,不少团体或单位按例开始往居民区、村里乃至工厂、船台送春联。人们脑子里早就酝酿好的春联就像花木的新芽,纷纷往外拱,等着栽种到家家户户。
写得一手好书法的人,一下子走红了,开始到处“赶场子”。写春联的地点多是在空旷场所:广场、公园、厂房前面、码头一角,等等。偶然一次,是在冬闲的大棚里写,四周立着柑橘、葡萄、枇杷、火龙果……无风,手就温软,写得更惬意。写春联的人衣着颜色多以炭黑、蓝黑为主,与墨同色系。他们四周张挂着一帘帘的春联,长桌、地面也被春联覆盖。碗大的墨字,纷纷落在洒金大红纸上,仿佛凭空生起了无数个火炉,无形的热力借助高饱和度的色彩传导出去。
人们陆续过来,先巡视一遍现成的,最后踱到长桌边,看正在写的。写书法的人一直在运笔如风,酣畅淋漓,无暇抬头,任来者观摩、评论。
光看春联,也能看出所在之处的地理特点。诗画象山仙子国,人文渔港寿星家;十分海鲜有风味,一曲渔光展风华……有趣的是,送往渔船的春联里多有“佳木争春成翘楚,朝花浥露吐新蕾”之句,一派田园风光,仿佛随春联送上船的还有一小方陆地。船上所贴,更常见的是斗大的福字,写在菱形红纸上。写福字比写对联效率高,一点、一横撇、一竖……“福”源源不断生出来,引人往美好处遐想。大笔饱蘸浓墨,一不小心滴了一颗墨珠在旁,正要作废,来者忙说:“给我吧,福多一点,好!”
这些福字被船主亲手贴上舷窗玻璃。公历年头、农历年尾,有人送福上船,好兆头,渔民们心情愉悦,满面春色。当渔船成群泊在石浦港的时候,从渔港马路走过去,好似走在红彤彤的春风里。还有些福字写在镶金边的红色硬纸上,自带红色中国结为穗子,方便挂进厅堂。要红火,就不只高山大海,还要由外而内。
一副好春联,字形和内容须是形质兼美。一旦被人盯上,端着就走,像捧了贵重物品,生怕沾染、折皱。特别讲究的人,自己带了句子来,好比自备食材的食客,仅让厨师代为加工。印象最深的是位老先生,年年都来,今天穿了军绿色连帽毛呢面羽绒大衣,脚蹬白底黑面高帮旅游鞋,板寸头,肩背笔挺。他自备的句子一成不变:门纳春夏秋冬福,户趁东西南北潮;横批:年年胜景。邻居笑他:“这好比一模一样的衬衣买了几打,你虽日日在换,我们看来年年不换。”他却毫不在意。唯一于不变中求变的,是他每年留心找不同的人来写,形可不同,意必相同。
春联迟早都会被大家争抢而空。一位壮年男子赶到时,场上已无春联剩余。这位男子在写春联的桌子前转了一圈才搓手站定,笑眯眯地看着众人说:“我刚从城里回村,路上耽搁了一下,所以来晚了。刚才远远看过来,这里一片红火,我以为还有不少对子呢。”原来这批写春联的人为了防冻,也为了图喜庆,个个在脖子上围了一色的大红羊绒围巾,护得身子暖洋洋的,也映得场上红彤彤的,不承想被这迟到的男子,远远看成了春联。大家回以善意的哄笑,笑声中便有人重新拿出笔墨,要为这位男子专门写一副。
当所有新春联各就各位,换下贴了一整年的旧春联我更愿意将它们看成花儿,绽放在人家的门户和船上,先于春天令世间生机勃勃。让回家的人、尚在漂泊的人,无论何时何日,一抬头,先是耀眼的腊月红,再是温暖的祝福。
窗花舞
张金凤
是谁在乌黑的窗棂上铺展一派春意?是谁在漫天飞雪里开出一枝红梅?是谁经过剪刀轻灵的裁剪,给家中增添喜气洋洋的期待?是窗花。
我去赶年集,总是特意寻找窗花。那手工剪出的红窗花,每一幅都经由一双灵巧的手抚摸过,充满智慧和爱意;剪刀裁出的线条简约而质朴,有着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窗花承载着我美好的记忆。幼时乡下的冬日,红彤彤的炭火盆旁,女人守着针线笸箩,用小剪刀在红纸上勾画自己的梦。剪了一辈子窗花的奶奶,头白了,耳背了,眼花了,可仍能剪窗花。她说,剪刀有眼睛,心里有图谱。她戴着花镜盘腿而坐,小巧的剪刀在指尖轻盈地旋转、舞蹈。左旋右转之间,一朵朵美丽的窗花在她手中慢慢绽放:牡丹花团硕大、富贵华美;荷花在清澈的野塘袅袅出水,鲤鱼蹦出水面;怀抱大鲤鱼的胖娃娃,肉嘟嘟的脸上带着笑;园圃中,菜花尖上有蝴蝶、蜻蜓生动地伫立……剪着剪着,奶奶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光,勾起了她对劳动岁月的记忆,嘴角笑起两朵花儿。她剪出肌腱有力的农夫扬鞭驱健牛耕田,剪出忙于秋收的老者赶着满载的马车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她也剪出悠然自得的休憩场景:戴斗笠的老人垂钓于湖畔,一圈圈细红的曲线就是湖水的涟漪;摇蒲扇的奶奶、纳鞋底的妇人在大树下安详地微笑,用故事拴住一帮穿肚兜的娃娃……
日头升上来又落下去,窗棂纸暗下去又亮起来。那些盛开在笸箩里的窗花,耐心地等着好日子到来。
除夕的日子要重新封窗。棂子窗的木头骨架早被烟火熏染得结实而黝黑,初秋封上去的窗纸已经泛黄。它们被风摩挲过,被寒雨拍打过,被麻雀的嘴啄过,被小孩子的手指尖捅破过,一个个生动的日子都在它们身上留下痕迹。到年关,女人们刮掉旧窗纸,给窗棂掸去尘埃,贴上崭新的白纸。那雪白的新窗纸,将覆盖过往日子里的辛劳,给平实的生活增添浪漫。
新封的窗太素淡了,像茫茫的雪野,要开些花儿才有生机。过了年,春天就到了,是应该红红火火地开着花迎接它。于是,人们将红彤彤的窗花张贴在雪白的窗纸上。年轻人的新房窗上贴的是鸳鸯戏水、喜鹊登枝、麒麟送子,从晨曦微明到月笼西窗,每一次抬眼看,窗上都流淌着幸福。姑娘们的窗上贴着嫦娥奔月、天女散花、百鸟朝凤,这是她们自己剪的,把自己的心气和期盼都张贴在窗上。住着学生娃的屋子,窗子常常是无形的教科书,窗花有闻鸡起舞,有精忠报国。老人居住的窗上则贴着桃园结义、孟母三迁,老故事里的人生哲理,是一辈子的念想。
火红的窗花,把风景、传说、戏文搬到窗上来,把所有的念想和期盼都凝聚在窗上。窗花是枝头飞翔的诗歌,是心头传承的薪火。
每年春节前,我都抽空剪几幅自己的窗花。如今的窗已经是宽大明亮的玻璃窗,窗花也由方寸宽窄发展到锦绣花团。
我的窗花师父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,每年在老城区的石桥边卖窗花。十几年前她全家从农村迁到城里,离了土地,就在家剪窗花分给亲戚朋友。后来不断有人联系购买,这乡村里的老手艺竟然被城市人接纳和喜欢,于是她把剪窗花做成了自己的事业。平日里订购大图的居多,比如给老人祝寿的“松鹤图”,挂新屋的“大吉图”(雄鸡)、“百财图”(白菜)等。过年的窗花大多小巧,但是她最愿意剪这一类,边剪边想着一幅幅“喜鹊登枝”“狮子把门”“生龙活虎”都会贴在什么样的窗上,祝福什么样的人家,心里就欢喜。
老人的窗花有传统的样式,也有女儿给设计的新颖花样。我买窗花都是买双份,一份贴在窗上,一份收藏。慢慢地,自己也学着剪。从最简单的花样开始,从笨拙渐渐娴熟,线条由粗陋渐渐圆润,有一年,竟也剪出几幅颇为满意的白菜图,过年前分给亲友们张贴,皆大欢喜。
去年我买了一套胶州秧歌人物的窗花,共十二张,有小嫚、扇女、翠花、鼓子等,人物栩栩如生,动作鲜活动感。把它们一一张贴到窗上,屋里登时热闹起来,就像在炕头上演了一场秧歌大戏。新年的阳光里,这些窗花就像活的一样,彩绸飞舞,扇子翻飞,耳畔似乎响起锣鼓唢呐的欢畅曲调。
不经意抬头往外看,见对面人家的玻璃窗上也贴着这种窗花。小区喇叭里响着热闹的《春节序曲》,屋角的红灯笼在风里晃动着。那一刻,我感觉窗花上的舞者都在舞动,舞得旖旎多姿,舞得虎虎生风。团团祥和的喜气笼罩着家家的春节。
社火迎春
乔忠延
江河行地,日月经天,城乡面貌日新月异,古老的年俗却桃花依旧笑春风,鲜活在临汾大地上。
闹社火,就是临汾不变的风俗。如果说年夜饭是一家人欢聚的大团圆,那闹社火就是全村人欢聚的大团圆。大年初一,放过亮响响的鞭炮,吃过香喷喷的煮饺,穿新戴洁的后生,穿红挂绿的姑娘,还有天真可爱的孩童,都欢聚到村中的广场上。银须老爷爷、白发老奶奶脚步虽然不如年轻人灵动,却也赶来了,或拱手揖礼,或脱帽鞠躬,团拜一过,社火即闹腾开来。打起锣鼓,扭起秧歌,跑起竹马,舞起狮子,老老少少的欢声笑语也飞扬开来。
欢声笑语最响亮、最激昂的时刻,一准是在跑鼓车。两架鼓车,两拨后生,在跑道的左右分别就位。每架车上竖一面大鼓,一个壮汉手持鼓槌牢牢站定。车前一个彪形大汉早已双手掌住车辕,辕把前十个小伙子甩掉棉袄,拉起襻绳,一律弓步待发。一声炮响为令,随着周边众人的呐喊,眨眼间两架鼓车如离弦之箭,窜出好远。车上鼓手猛擂,车下后生猛跑,争先恐后,只为拔得头筹。跑得浑身冒汗仍在猛跑,跑得头冒热气仍在猛跑,这班人刚刚跑得吁吁气喘,已有人钻进拉车的行列飞速替换。鼓车过处地上轰隆隆震荡,身边风声呼啸,耳畔山呼海啸,恍若地动山摇……
突然静了下来,静得鸦雀无声,这一准是开始登天塔了!天塔是用板凳当场搭建的高台,左一条右一条,横一层竖一层,层层摞高,摞高,搭建者已站在高空飘摇了,板凳还在摞高。仔细看,不是人在飘摇,而是头顶上的白云在飘摇。看看,称作天塔毫不夸张吧?正愁搭建者如何下来,忽然如风摆杨柳,人已顺着塔边滑落在地。不待喝彩声响起,四只色彩亮丽的“雄狮”,早蹦跳出人群,沿着天塔四个角同时上攀。攀一层,勾腿侧身,面朝天空摇头晃脑,似乎在抒发凌云之志。再攀一层,背负蓝天,朝下观看,犹如展翅大鹏俯瞰人间。不觉然,四只“雄狮”已蹦跳上天塔的顶端。看看那高耸云天的架势,仰头观望的人哪个不敛声屏气,真真是“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”。可这不知高低的“雄狮”偏偏还要腾空蹦跳,似瑶池摘星,如天马行空。表演者艺高人胆大,观赏者却禁不住提心吊胆,手心出汗!
孩提岁月看过无数次跑鼓车、登天塔,只觉得过瘾、刺激,却丝毫不明白父老乡亲为何要玩这一把心跳?年事渐高,阅世渐多,逐渐悟出这跑鼓车、登天塔,是乡亲们满腔豪情的喷发,是在展示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”的壮志!
白天里的闹社火就够红火了,可夕阳西下后的热闹才更让人期盼。夜里的欢腾要让人看得见,就必须请出灯笼。灯笼是个妙物,既让人看得见,又不让人看得那么真切,迷迷蒙蒙,亦真亦幻。当然,只把灯笼提在手里,是映照不出这样如梦似幻的光景的。于是,长长的竹竿将灯笼挑到梢尖,高高擎起,温润的光色便映亮周围一片。细看,这灯笼妙不可言,不只是椭圆的、四方的,还有用竹子扎成的黄牛、玉兔、骏马……十二生肖云集,装点夜色,散发光亮,映照出醉人的景致。
灯笼装饰着社火,社火催化着灯笼。先前是百家百户各自带灯,谁都可以高擎灯笼闹社火、看社火。后来,高擎灯笼有了讲究,谁家新娶了媳妇、新添了人丁、新盖了宅院、新考上大学,才有高擎灯笼的资格。看吧,高擎灯笼的人满脸喜气,观赏表演的人喜气满脸,红红火火,何等壮观!
临汾的父老乡亲,把灯笼叫作“高照”。看到此处,你一定理解这称呼的由来了吧?高照,高高照亮了闹社火的场景,高高照亮了烟火人间。你看那高擎灯笼追逐鼓车的人群,一路奋跑,蜿蜒成了一条腾飞的火龙;你看那高擎至天塔上的九个灯笼,簇拥一团,散发着温润的红光。光色映红了每一张仰头观望的笑脸,如同一朵朵绽开的春花。春花簇拥,春花斑斓,交织出一幅心花怒放的秀丽画卷。
临汾春烂漫,春天欢笑着到来了。
头顶的云彩
吴昌勇
陕南腊月,当野桃花信使般将春归的消息传遍山冈,天空日渐温润,灰蒙蒙的云朵如积雪消融,久违的湛蓝潮涌到远山之巅。
春气从大地升腾到头顶,揭开绒帽,手指插入发丝的瞬间,分明感到:该理发了!几乎在同一时间,乡亲们想到了传统的年俗之约。辞旧迎新,一定要为自己和家人讨个好彩头。
打我记事起,腊月的最后几天,爷爷家门外的小院坝就是一个露天的乡村理发馆,四叔是村里人都认可的业余理发师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四叔刚二十出头,浓眉大眼,高中毕业后在乡里上班。工作闲暇,他总爱到镇上理发馆转悠,日子久了,也照猫画虎般学到点理发的手艺。也因是理发馆的常客,他可以让理发师按自己的脸型设计发型。先洗,后剪,再吹,末了打上定型的发胶,乌黑的头发洋溢着青春气息。村里人都夸四叔时髦,都说他的精气神全在头上。
起初,四叔怕手艺不精,会让结伴而至的乡亲失望,只笑不应。一番推辞过后,曾是村里剃头匠的爷爷慢腾腾递话道:“邻舍都相信你哩!沉住气,莫急莫慌,心明眼亮,推子握紧搭平就好。”见此情景,四叔笑盈盈地应一声:“哎,记住了。”话音刚落,已转身开始准备。
等到炉火烤得乡亲们满脸通红,火炉上铁壶的壶盖也被蒸汽掀动得嘭嘭作响,四叔起身,拎了椅子和围布走向屋外。我亦起身,提着铁壶紧跟在四叔身后,先在脸盆里兑好温水,再将理发推子擦得锃亮递到四叔手上,镜子也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。
不用抓阄,理发的顺序装在每个人心里。轮到自己了,摘掉帽子,拿一把木梳子将窝蜷的头发梳顺后,紧憋一口气,把头扎进脸盆,犁耙般的手指反复抓挠搓洗头发好几遍,直到洗头膏泛起满头雪白的泡沫。站在一旁的四叔,示意我从水桶里舀出一瓢瓢温水为乡亲们冲洗头发,再递上擦头的毛巾。
进入角色的四叔,一下子神气起来。不论年龄,也不论辈分,他一个劲儿地叮咛:“稳住,莫乱动,当心推子伤了头皮。”只见他跨开双脚呈“八”字状,一把桃木梳子将湿头发梳顺,目光绕着头顶细细端详一番,左手搭在头顶,握在右手的推子从脸颊、从耳畔、从后脑勺向头顶缓缓推移。连接左右手柄的一副压缩弹簧,咔哒咔哒地传导着四叔指间的力量,也让推齿伴着手掌和弹簧的松紧节奏,在潮湿的发丛中穿梭。四叔憋足劲儿,鼓起腮,不时吹落一绺绺剪掉的头发,并左右移动视线,仿佛正在创作一幅炭笔素描,在对强弱、明暗、虚实的修正中,让发际线尽可能立体、流畅。
半个钟头左右,四叔紧绷的面部表情变得松弛。我赶忙拿起镜子递到乡亲手上。他们端着镜子左照照,右看看,瞧见棱角分明的一头短发,咧开嘴,笑着夸赞四叔的好手艺。
想想也是。乡亲们辛苦了一年,虽然平时也理发,但只有到了年根,才能腾出时间细细拾掇自己。他们用手在头上反复摩挲,散着热气的头顶,似乎有一片柔和的云彩,在跳跃,在铺展,在弥散。
那一刻,四叔握在手中的仿佛不是推子,而是一支温水泡开的毛笔,在每个人的头顶绘出辞旧迎新的精气神。他努力让每个人容光焕发地走进新年,让明媚的春光洒落每个人的头顶。
多年之后,四叔在县城有了自己的新居。他时常念叨,现在生活好了,每天都在过年哩。而今,镇里和村子的理发馆外,炫目的霓虹灯日夜旋转。添了白发和皱纹的四叔,不忘抽空去理发馆打理一款和年岁相称的发型。任凭时光变迁,“从头开始”的年俗不变,为生活讨个好彩头的期待不变。每临年关,四叔依然会去楼下临街的理发馆,坐在舒适绵软的转椅上,如听话的孩童披上围布。理发师手中的电推剪嗡嗡作响,好似天际传来的春雷。
望着明亮的墙镜和镜中自己的发际线,四叔仿佛看见一团祥云升腾而起,越过头顶,越过楼宇。此时此刻,盛世祥和的祝愿,尽在和四叔一样热爱生活、珍惜生活、创造生活的万千劳动者的展望和憧憬里,如头顶的五彩云朵在春风里飘荡。